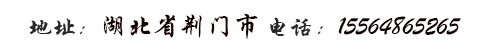我哥,娶了我爱的人
|
魏涉还是来见我了。灵堂内阴风瑟瑟,梁柱上的白绸肆意纠缠,烛火明明灭灭摇曳不停。我跪在魏延棺前,往火盆内添了一把纸钱,仿若没有听到身后或轻或重的细微声响。夜色浓厚,万籁俱寂,他负一身清冷月色立于廊下,良久,终是上前轻声唤我:“大嫂。”我手中动作顿了一瞬,待身旁的蒲垫深陷,着玄色官袍的身影沉默而跪,我才缓缓将视线移到他的身上。算起来,我已经有三个月没见过魏涉了。上次见面时还是初春,魏延远在边疆,他便代兄长携家眷登山礼佛。那时岐山的桃花开得正好,团簇如霞,落英缤纷。我坐在轿中掀帘唤他,盈盈笑道:“烦请魏侍郎折几枝桃花来。”我与魏涉相识的年份其实是早于魏延的,所以这不太守礼且带了几分戏谑意味的“魏侍郎”的称呼,倒也无人置喙。彼时他一身青衣,骑马立于斜桥处,回首间,春风吹散鬓角几缕碎发。他亦朝我笑,嘴角荡起浅浅梨涡,朗声称好。只是我从未想过,那时远在边疆的夫君魏延,会在三日后被圣上派去攻打蛮夷的南方边境。他只有三千魏家军,且无粮无援,无策无谋,满朝文武皆知,此战只为转移敌军西疆战场的兵力,多半是有去无回。而这一切,皆因魏涉一纸奏折的举荐。二哥将此事说与我听时,我并不相信。直到在向来稳重的大哥那里证实,我才如晴天霹雳,只觉心如死灰。二哥还说,如今朝中众臣私下纷议,说魏涉嫉恨兄长承袭父亲爵位,为满窃位之私心,操戈于室,贻笑外人。若其父魏承山仍且在世,定是不认这等不忠不孝的孽子。我自以为了解魏涉的为人,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,他为何会行事至此?当真是嫉恨兄长承袭父亲爵位,还是要扫平障碍另立门户?纸钱燃尽的烟气太浓,闷得人喘不过气,我捂住心口急咳一声,声音在空荡的灵堂内显得极为清晰。魏涉直身跪在魏延棺前,闻声侧身看来,眸中浮出一抹忧色:“兄长乃我魏家将门之后,战死沙场实为英雄豪杰,大嫂如此悲痛,他泉下知晓,当会不安。”我只当他太会做戏,右拳攥紧又松开,猛然抽出藏在蒲垫下的利刃,狠狠抵于他喉前。我望着他这张与魏延七分相像的面庞,一字一顿道:“魏涉,你魏家满门忠烈,世代英豪,怎会出了你这样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辱没家门!”剑尖刺破他喉间细脆的肌理,沁出一条血线。他抬手紧紧抓住锋利的剑刃,鲜血从他掌心一滴滴落下,落在我素白孝衣的裙摆上,宛如绽放出朵朵嫣红寒梅。他叹了一口气,如安抚般轻声唤我:“阿尧。”其实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叫我了,我愣了一下,仰面望向他,恍惚间好像想到了什么,嘴角扯出一抹讽刺的弧度,笑得癫狂。我问他:“魏涉,你这样做,不过是因为你喜欢我,对不对?因为魏延死了,你就有机会了,对不对!”他幽深的眸中终于有了波澜,我只觉手腕一麻,利剑“咣当”砸落在地上,右手便被他的大掌紧紧禁锢。“你可知道,你在兄长灵前说了些什么浑话?”他身躯逼近,清冷的熏香气息铺天盖地迎面而来,瞳色清亮,眸中似有微光忽明忽灭。我已经许多年,未见过魏涉这般喜怒形于色的模样了,就仿佛,一下子回到了十四年前,他还是我最初识得的那个俊朗少年,那个站在河岸边清浅含笑,如若春风的魏家小公子。父亲四十岁才得我,上头几个哥哥,独我一个女孩,我被他娇宠纵容得不成样子,那时京城里的达官贵人皆知,相国卓漓光的小女儿卓清尧顽劣野蛮,不守教法。每每听闻这些说法,父亲总是摸着我软软的发顶笑道,我卓漓光的娇娇女儿,我疼爱,关旁人何事?凭着父亲这句话,我在年少无知时做了不少荒唐事,直到十岁那年,我与刚刚八岁的魏涉发生争执,使他失足落入易河,得了教训,才有所收敛。我记得那是元启二十年的上元节,我扮作少年模样,甩掉身后的家仆,跑到易河边上放河灯。谁知遇到无良商贩,卖给我一只破洞河灯,却偏说是我故意弄坏讹他银钱。我气不过,卷起袖子站在河灯摊前与他理论,唇枪舌剑针锋相对,大有不死不休之势。周遭渐渐围起人群,却不知从哪传来一声嗤笑。我本就不悦之极,那笑声无异于火上浇油,竖眉循声望去,就见身后石阶上站着一个身穿白袍的小公子,瞧着模样尚小,清秀俊朗,此刻正笑着看向我,嘴角浅浅的梨涡若隐若现。“你笑什么?”我怒瞪他。谁知他笑意更甚,却并未理会我,只是从台阶上踱步而下,接过我手中的破洞河灯,朝那商贩问道:“你做河灯的彩纸是城南那家纸舍买的吧?”商贩不以为意地点头:“那又怎样?”小公子似乎了然于心,道:“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,城南纸舍纸浆不匀,常有残裂,除了这只河灯,你这摊上必然还得有破洞的河灯,不信……”说着便从一堆河灯里随意挑出一只,转身让围观群众查看。“看,真的有洞!”人群里顿时嘈杂起来,纷纷指责那商贩无良。商贩见状无法,只得连连向我认错,且将银钱退还于我。许久也没能解决的事儿却被这个少年三言两语解决了,我不由心生敬佩,却也生出一丝疑惑,便悄悄问他:“你是怎么一下就能挑出有破洞的河灯的?”远处荷花形状的河灯攒成簇簇,灯影幢幢,明明灭灭,衬得他面容温柔缥缈。他闻言回眸看我,有些窘迫地答道:“其实那个洞,是我拿手指抠的。”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有多震惊了,虽说我向来骄纵,但还从未做过这等坑骗之事,于是不由他分说,便拉起他的衣袖要拽他前去道歉。他当然不依,嘴里一边说着“我还不是想帮你”,一边使力将我甩开。这场拉锯并没僵持太久,他很快便从我手中挣脱,可也因为突然脱力没有站稳,猝不及防地向后仰倒,落入了身后飘荡着无数烛火灯影的易河里。当四处溅起的水花打在我脸上时,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几乎在他落水的瞬间,一行家仆模样的人便冲过来跳水救人。望着那群家仆衣袍上的家纹,我隐约有种自己闯了大祸的预感。元启二十年的上元节,令百姓津津乐道的不是晋王献给圣上一只城墙高的灯笼,也不是宫里最受宠的静妃诞下双子,而是在那天,以刁蛮娇纵闻名的相国小女儿卓清尧,把威武大将军魏承山的小儿子魏涉推进了河里。此举一出,满城哗然。我终是闯祸了。父亲虽贵为相国,但对保家卫国的武将极为敬重。平日里我招惹些别的官勋子弟也就罢了,如今却是满门忠烈的魏家。我生平第一次,见到父亲对我动怒。他怒时并不责骂体罚,只是沉下脸看着我,直至我垂下头忏悔认错,他面色才有所缓和,沉声道:“过两日我带你去趟魏府,你亲自向那魏家二郎认错。”这事并不容易。我犹记得那日魏涉从水中被捞出时除了冻得发抖的身体,还有眸中清晰可见的怒气。是个骄傲的让人难办的少年。这便是我与魏涉的初见,虽不愉快但也不至于结下什么深仇大恨。所以后来直到魏延去世前,他在我的印象里,一直是那个机灵聪颖的骄傲少年,哪怕他早已官拜高位,哪怕我早已无法看清他的内心。京城下了一场多年未见的大雨,雨后初晴,我站在水雾氤氲的院落里,听丫鬟长欢向我说着魏涉近况,恍若大梦初醒。自那日灵堂不欢而散,他便染上风寒,卧床数日。我去找他时正值午后,温暖的日光透过轩窗,轻柔地洒落到屋内每个角落。他阖目斜躺在窗下的暖榻上,白皙皮肤泛着温柔的色泽。我突然不合时宜地想到了很多年前,在我使魏涉失足落入易河后,也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午后,我到魏府向他赔罪。偌大的魏府空阔幽静,鞋履落在青石板上悄无声息,我经魏府管家指引,朝魏涉的院落走去。那时我当真礼数不周,只在门外唤了两声,便自顾自推门而入了。满室暖阳,静谧安逸,魏涉正靠在窗边小憩。我便在他屋里来回转了一圈,他却不知何时醒了,正直直看着我,眸中泛着刚睡醒后的水雾,充满警惕。我摸了摸鼻头,讪讪道:“魏涉,我是来向你道歉的……”他笑了一声,从榻上慢慢坐起,似是不屑般淡淡道:“便是你再道歉,全京城的百姓也都已经知道我出过的丑了。”我一时语塞,但仍朝前迈了两步,反问他:“那要如何?若是能回到那日,换我替你落水我也在所不辞!”魏涉不应,偏头不再看我。这态度让人无可奈何却又心生怒气,我想也没想便伸手钳住他脸颊两侧,生生将他面庞扭过来面向我。窗边帷幔随风曳动,轻轻拂过他晕出薄红的白皙面庞和略带迷茫的清亮黑眸。日晖明媚,风影绰约,我突然忘记了想说的话,一时愣住。待清风歇止,帷幔落停,他的眸色才渐渐清明,伸手狠狠将我推开。像是被我气极了,开始咳嗽连连,边喘边指着我鼻子恨恨道:“不知羞耻!”直至今日,我依然记得魏涉当时含羞带怒的模样,他那会儿年纪尚小,稚嫩的面庞圆润软糯,清亮的瞳色忽明忽灭,嘴里却说着不符年龄的话,毫无威严,分外违和,只是让人产生想要逗弄的心思。记忆与现实渐渐重合,多年前窗下小憩的那个小少年,似乎在一瞬间抽苗成长,最终变作如今成熟长大后的魏涉,此刻正用那双漆黑的眼眸,定定望着我。不知是我的到来将他吵醒,还是他本就没有睡着。他从暖榻上起身,却因动作太大,右拳抵在唇边低声咳起。好像从我认识他起,他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。我犹豫了一下,看到他右手包裹的厚厚白纱,愣了愣,才沉声道:“魏涉,我是来告诉你,魏家的爵位与家产,都是留给端儿的,我绝不会让你一毫,你也休想窥探半分。”他像听到什么笑话,竟勾起唇角轻笑了一声,而后扭头望向窗外。我随他的视线望去,雕花梁柱外,一群鸟雀叽喳掠过,飞向碧空,只留下极小的斑点。我听到了他的轻声呢喃,当真是极轻的呢喃。他说:“我已命不久矣,还要那些做什么呢?”其实我一直都觉得魏涉是个可怜人,他幼时丧母,自小身子便弱,我刚认识他那会儿,他父兄都远在边疆驻守,偌大的魏府,只有他和一群家仆。所以当年道歉失败被他赶出来后,我回望了一眼身后牌匾上龙飞凤舞的“魏府”二字,竟也生出一些别样的感觉。我嫁到魏家的这么多年,旁人都说我与魏涉关系极好,叔嫂之间从无龃龉,宛如亲生姐弟。可那些人不知道,其实很早很早以前,我与魏涉便已经颇为熟稔,关系亲近了。那时我在他眼里还是道歉被赶出来的不知礼数的姑娘,可我却像得了趣事,对这个满是鬼点子却惯装正经的少年上了心。后来我没事便往魏府跑,把自认不错的各类物什送给他,然而不管是珍宝名画还是锦缎玉帛,全都无一例外地被他原物奉还。我消停了一段时间,倒不是屡屡碰壁后放弃了,而是开始研究他的喜好。听魏府的管家说,魏涉虽看似年少老成不若孩童,其实最是想念远在边疆的父兄。于是我花了整整半月,做了一个他父兄镇守之处的战地沙盘,峡谷林木,河溪山涧,无一不注满心血。我将这礼物送给魏涉时,恰逢初雪之日。白雪繁飞,薄薄落于身上,天地间银装素裹,静谧无声。我站在魏府门前,双手护在嘴边哈气,抬头冲刚刚出现的魏涉咧嘴一笑。“魏涉你看,这就是你父兄镇守的地方。”我望着他,看到他眸中闪烁着的微光,郑重其事地说:“他们都是英雄。”他静静站在檐下,肤色被落雪衬得莹莹如玉,看向我的眼神终于柔软。后来魏涉告诉我,其实那个初雪之日是他生辰,若非如此,他必然不会收下我的礼物。那时我与他已经很熟了,便对此嗤之以鼻,说:“若换作如今的我,也必不会花费这么多心思为你准备礼物的。”这成了我与魏涉之后几年里最寻常的相处方式。他确实是个骄傲的少年,但打破这骄傲却成了我最大的乐趣。有时相约出门前,我在他背后偷偷贴上一张画着王八的宣纸,在他发现后追着我满院子跑。或者趁他不备,我把偷来的姑娘荷包塞进他的衣袖,待那姑娘含羞带怯地望向他时,他才察觉异常,然后狠狠瞪向早已笑得直不起腰的我。我那时化名“姚清卓”,常以男装与他同行,他心情好时会唤我“阿尧”,旁人只当我是他的好友,倒也省去了流言蜚语的烦恼。嫁给魏延后,我常将我跟魏涉间的趣事说与他听,他听后只笑说:“所谓一魔自有一魔降,说的便是你俩这般冤家对头吧。”那时我们刚成婚不久,公爹尚在,魏府还未分家。我偶尔能在府中遇到魏涉,他总是低头叫声“大嫂”后便仓促离去。我只当他心中别扭,毕竟相识多年,他从未想过我会成为他的大嫂。就像我也从未想过,有一天我爱上的那个人,会是他的兄长。元启二十四年,魏涉的父兄率兵回京复命。我提前预订了春风楼三层靠窗的位置,只为看清扬名天下魏家军的威武不凡。待蜿蜒大军行至楼下长街之时,我兴奋地从雕窗探头望去。铁骑铮铮,气势轩昂,最前方带兵的是一位年轻将军,身着玄铁铠甲,牵胯下高头战马。似觉察到我的灼灼目光,他猛然抬头,穿过人海人潮,遥遥望了过来。与他相视一霎,我只觉喧嚣长街顷刻寂灭,眼前只留他一人。我无比清晰地听到心头跳动,如石子落入湖心,涟漪不止,波澜阵阵。率领魏家军的年轻将领,与魏涉七分相像的面庞,我几乎一瞬间就想到了他的身份。威武大将军魏承山的长子,魏涉的兄长,魏延。在遇到魏延之前,我曾一度以为,这世间所有男子都和京城的公子哥们一样,白袍玉面,清秀单薄,平日里只会饮酒作诗,挥洒笔墨。所以在那惊鸿一瞥后,我毫不顾忌女子的娇羞矜持,再去找魏涉时,总会借机与魏延搭话。我依然作男子打扮,他便当我是魏涉好友“姚清卓”,待我与魏涉无异,甚是照拂。见面次数多了,熟络起来,他便带我们去演练场骑马,偶尔也教我们射箭。有次我差点从马上跌落,幸被他飞身揽住,才得以安然无恙。日子久了,初时的悸动早已化作一往情深。刚刚及笄,情窦初开的年岁,我眼中只有魏延一人。我以为这件连魏涉都没能察觉到的事,只是我一人知晓的秘密。可我还是没能瞒住父亲。那时已经是暮春,父亲上完朝回府,恰好遇见出门参加百花茶会的我。我听说魏延也会赴宴,欲向他表明身份,便穿了一袭嫩粉衣裙,发髻齐整,略施粉黛。父亲见状先是一愣,而后了然于心地笑着问我:“不知是哪家公子得了我娇娇的芳心?”彼时府中梨花早已落为春泥,我却好像又嗅到了淡淡梨花香,羞怯地垂眸答道:“不知父亲识不识得那魏家长子,魏延?”在我年少浅薄的认知里,相国之女与将军之子的姻缘,定是说书人口中才子佳女门当户对的风月佳话。可父亲沉默了一会,而后眼神复杂地摸了摸我的发顶,沉声说:“你若嫁入魏家,日后,为父怕不能保你一生喜乐顺遂。”我那时不懂父亲的意思,只当他道勋爵贵胄家规矩森严不能容我任性胡来,便满心欢喜地摇摇头说:“我不怕,再说不管嫁给谁,父亲也不能护我此生啊。”我那时不懂,权臣将相间的联姻,是强强联手、稳固权势,也是木秀于林、树大招风,若有一日皇帝忌惮打压,必将首当其冲。而这个道理,我竟花了半生才明白。父亲从未拂过我的意,在我表明心意后不久,他便在府中宴请朝中同僚,其中便有魏家父子。那日魏延一身薄衫青衣,无端多了些许的书卷气。他那时已经知晓我的身份,也隐约猜出我的心意,却迟迟未予答复。席间我有些烦闷,便借故离去。月上梢头,我静静站在荷塘边,身后传来鞋履落于石板的浅浅声响,循声望去,就看见魏延手持玉佩立于一棵柳树下。清风徐徐,荡起柳枝拂面,他笑了笑,抬脚朝我走来。走到我面前时他顿了顿,带着些拘谨地问我:“我可以像涉儿那样,唤你阿尧吗?”清浅的月辉散落在他的面庞上,如薄薄一层雾气,虚虚浮动在我面前。我望着他俊毅的面庞,羞涩地点了点头。他又笑了笑,把手中的玉佩放到我的掌心,一字一顿地说:“阿尧,这个玉佩娘亲留给我的,让我日后送给心仪的姑娘。”时至今日,我仍能记得那日朦胧月光下魏延高大的身形,他长我四岁,又做惯了兄长,自元启二十五年嫁给他后,我被照顾得无微不至,处处妥帖。十年夫妻,我从未忘记过他在月下表明心意的模样,也从未忘记我那时暗暗下定的决心。无论以后喜乐与否,顺遂与否,我都会陪伴魏延一生。可是魏延却死了,他的生命,永远停在了三个月前的春天。留下了我和尚且年幼的端儿,还有一片狼藉的魏府。没人会想得到,这一切只是源于魏家兄弟间的阋墙之衅,大约父亲那时说的是对的,我后半生的喜乐顺遂,他是保不住的。也没人保得住。可我又想,便是这半生如此仓皇无措狼狈不堪,还有端儿能给我念想。他如今八岁,同我初识时的魏涉一般年岁。清秀俊朗,面若冠玉,笑起来嘴边有浅浅的梨窝。但我罚了端儿。正午烈日当头,沉闷无风,路上的板石都似乎被蒸出汗液。我静静立在廊下,望向跪在院中倔强单薄的身影,心中又恨又疼。一旁的长欢犹犹豫豫地劝我说:“夫人,小公子都跪了一上午了……”我看了她一眼,她忙闭上了嘴。我揉揉额角,顿了顿,还是开口说:“让他起来吧。”话音刚落,端儿便被一群家仆扶着站起来,蹒跚着朝我走来。汗滴顺着他稚嫩的面庞滑落,黝黑的双眸湿漉漉的,却尽是倔强的神色。我鼻头微微一酸,往前走近两步,抬手用帕子擦去他额头的汗水,轻声问道:“知错了吗?”他突然伸手抓住我的前襟,双腿还带着久跪后的虚浮,仰面望来的眼神尽是倔强:“我本就无错,那夫子说我魏家功高盖主、拥兵自重,娘亲如何不知那是欲加之罪?我只是教训了一下他,我没错!”我看着他,恍惚了一下。魏延战死沙场才消去皇帝对魏家的忌惮,他是魏延之子,这些世人皆知的事实,却唯独他说不得。我狠下心,高高扬起右手,带起一阵凌厉掌风,他应声闭目。巴掌落下之前,高抬的手腕被却人紧紧抓住,我回头望去,就见魏涉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后。烈日炎炎,他却身披一袭黑色大氅,面色苍白得可怕。自那日我去他府上告诫警示后,已有些时日没见到他了。他轻咳一声,语气有些无力:“大嫂。”见来者是他,端儿眸色瞬间变得光亮,忙跑过去拉起他的手掌,语气雀跃地唤了一声:“二叔!”我看着端儿雀跃的模样,狠狠咬住嘴唇,明明魏涉已经算是他的害父仇人,可我还是不舍得告诉他事实,让他在仇恨中成长。魏涉放开紧握我手腕的手,轻轻放到端儿的发顶,温柔地揉了两下,才神色轻和地说:“二叔有话要同你娘亲说,你先回屋歇会儿吧。”端儿向来最听他的话,心里虽有不悦,却还是一步一回头地乖乖回屋了。日头灼热,晃得我脑壳一阵一阵地疼,我看向魏涉,猜想着他要同我说的话。可他只是望着端儿离去的方向,良久,才轻声开口问:“大嫂还记得端儿出生那日吗?”我怔愣了一下,但也仅仅只是一下,而后便轻笑着问他:“魏涉,你是想让我记起你的恩情吗?”他定定地看着我,我想大约是日头真的太过晃眼,我竟觉得他的眼神有些悲戚。他便这样沉默地望着我,直至疾风骤然吹过庭院,林叶大乱,才慢慢转身离去。我望着他明显消瘦了的背影,视线渐渐变得模糊。自我与魏延成婚后,魏卓两家确实在多年间相互扶持。将相联姻,贵府权门,一时间在朝堂内外皆是风光无限。只是端儿出生时却是个多事之秋。元启二十七年,先帝驾崩,新帝继位,次年改年号盛平。新帝年少,摄政掌权的实为晋王。盛平初年,公爹魏承山不幸战死沙场,为了镇守国境,晋王开始重用刚刚承袭父亲爵位的魏延。给他兵权,拨他军饷,让他前去征战西疆。那时京城正值大雪纷飞,我挺着肚子手捧暖炉坐在屋里,透过小窗往外看去,厚厚一层洁白积雪,几乎埋没了丫鬟半截小腿。临盆几乎就在一瞬之间,府中上下皆是手忙脚乱。耗了两个时辰生下端儿后,我的意识渐渐变得模糊不清。我嘴里喃喃念着魏延的名字,朦胧中似乎看到了他守在我身边,轻轻摸着我的鬓发唤我阿尧。之后我就再没了意识,只知道自己越来越来虚弱,我当时想,如果我没了,我的孩子该怎么办?但我看到了第二天大雪初停后浩瀚碧蓝的天空。后来我听长欢说,那晚是魏涉拿他魏家的军功向晋王求来太医,几乎整个太医署都被请来了魏府,焦急忙碌了一夜,才保住了我这条性命。长欢说这些话时,我只想着一定要好好谢谢魏涉。倘若当时我能聪慧一些,就很容易明白,向晋王求请太医这件事,会给魏家埋下多大隐患。拥兵自重,怙恩恃宠。已在官场浮沉了几年的魏涉不可能不知道其中要害。可那时的我根本想不到这些,只是踏进雪后的院落,抱着襁褓里的端儿靠在魏涉屋前的雕花门框上,抬头朝他笑道:“魏涉,谢谢你。”他见状匆匆向我走来,拿过一边的大氅披到我身上,蹙眉问:“这样冷的天怎么到处乱跑,若要见我,让丫鬟通报一声便是。”我低头“嗯”了一声,他的眼神渐渐柔软,笑起来眼睛眯成弯弯的模样,嘴角浅浅的梨涡如静水落石,荡漾成波。我那时已经很久没看到魏涉这么笑了,他抬手轻轻点了点襁褓里端儿的鼻尖,引得他不安地拱了拱。我恍然想到,嫁与魏延这么多年,我从未听魏涉说过心悦哪家姑娘,也从未见他身边有一二红颜。我曾劝他找个体己人早些成家,却被他用随意的说辞打发。为此我着实沮丧了一阵,怪他不若从前待我那般真实诚恳。可我也明白,从成为叔嫂那日起,我与他便隔了一层俗世枷锁,即便再为亲近,大约也是不能如从前那般无间了。傍晚时分,我犹豫着还是去了端儿屋里。他卷起裤管后的双膝乌青发紫,轻轻一触便疼得落泪,可他却硬生生咬住嘴唇,唯有乌黑双眸蓄满泪光。我鼻头酸得厉害,却只是沉默着为他上药。恰好这时父亲差人来传话,说是想端儿了。儿时他最是疼我,如今爱屋及乌,待端儿更是极好。于是次日我便带端儿回了卓府。端儿刚被我罚过,乖乖坐在一旁看我陪父亲下棋,闲聊之际,我恍惚间只觉得岁月静好,闲适安然。只是临走时,父亲突然叫住我。他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凌乱,一步步走近,就像当年我出嫁前离开家门前那样,轻轻握住我的手,沉默良久,他才再度开口,声音涩哑道:“阿尧,日后父亲不在身边,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”我点点头,转身上了轿子。回去的路上,端儿在我怀里睡着了。我也半阖双目,身体随轿子上下颠簸。我突然想到多年前出嫁那日,我也是这样坐在轿子里,从卓府沿着朱雀街,跨过易河上的平营桥,穿过大半个京城,被抬进了魏府。那晚我盖着大红盖头,端端正正坐在红烛摇曳的新房里,满心甜蜜地等待魏延的到来。有人推门进来,没有想象中众人簇拥闹洞房的喧闹,屋里很安静,只有一个人轻轻的脚步声。我在盖头下什么也看不到,但仍是羞着脸喊了一声:“魏延!”来人脚步声顿时停住,我以为是自己太过热情吓到了他,于是怯怯地掀起盖头的一角抬头看去。魏涉就站在屏风旁边,正愣愣地看着我。其实那时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过他了,从我和魏延订婚之后,我们成了世人眼中的叔嫂。只是我还没有为人长嫂的意识,仰仗着与他多年来的熟稔,毫无避讳地掀起半边盖头,问道:“魏涉,你兄长呢?”他这才回过神,局促不安地四处张望,步履慌张地往外走:“他还在外面喝酒,我……我去替他挡……”我只觉得他莫名其妙,但到底是新婚之夜。等到魏延归来拿秤杆挑了我的盖头后,在喜婆的贺词和亲朋的祝福之中,我抬眸羞怯地望向面前这个我托付终身的男人。我以为从此以后,我便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了。但也仅仅是,我以为。从我嫁到魏家起,魏卓两家便因联姻之名,一步步走向险象环生的昼锦之荣。我本不聪慧,我本不想参与政治权力间的斗争,可处在漩涡中多年,我终会被推向名为成长的深渊。盛平四年,晋王夺权落败,皇帝终于掌权,无论世间如何安详和睦,朝堂上总是在弥漫着权力更迭的阴云诡谲。或许是当年那个少年皇帝见过太多国戚权臣的肮脏手段,即便那时羽翼尚且未丰,却早已深谙权数之道。存在联姻关系魏卓的两家,位尊势重,权倾朝野,无疑被他深深忌惮。只是卓家是开朝元老百年世家,家族兴旺树大根深,所以皇帝的矛头,首先指向了曾受晋王重用,且如今人丁单薄的魏家。这四年来,在皇帝的有意打压下,魏府已然势薄没落,我做好了皇帝收回兵权贬谪魏延的准备,做好了父亲明哲保身置身事外的准备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,给魏府致命一击的人,竟然会是魏涉。我不知魏涉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下那纸奏折,又是如何拿捏住皇帝的心思,让他找到了最好的借口派魏延去打那场险极之仗——魏涉不愧出自满门忠烈的魏家,胸有大义,不拘小情。他作为胞弟力荐魏延,朕又岂能辜负?魏涉倒是因“胸有大义,不拘小情”得到了皇帝的嘉奖和赏识,消除了皇帝对魏家的忌惮。可这一切的代价,却是让魏延的生命,永远定格在了盛平八年的春天。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,如果当年我嫁的不是魏延,而是任何一个别的官宦家的子弟,那么如今的结果,会不会有所不同?可是这世上,最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如果。这些日子,长欢总在我耳边提起魏涉府里的事儿,又出入了多少名医大夫,又得了些圣上的何等赏赐。每每此时,长欢总是犹犹豫豫问我要不要去看看他:“夫人有没有想过,或许没有二爷举荐,圣上也有可能让大爷去……”我笑了笑,摇摇头道:“夫君毕竟是保家卫国的英雄,圣上就算是忌惮,说到底也不过是收他兵权,贬他官位。”我顿了顿,继续缓声道:“至少,他还能活着。”然而饶是有皇帝的嘉奖赏赐,魏涉的身子却越来越差了。我最后一次见到魏涉,是在盛平九年冬日里的某个雪天。那时京城已经很久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,百姓迎春,爆竹声声,可他府中却尽是落寞萧条。我推开门时,魏涉正躺在床上,两旁厚厚的帘帐将他虚掩,屋里很暗,我只能看到他的剪影。苦涩的药草味道充斥鼻腔,我站在门前,远远望着他。似乎是察觉我的到来,他的身影动了动,随之而来的却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咳。我像忘记了我们之间所谓的仇恨,一步步朝他走去。他并没有动作,只是双眼空洞地望着帐顶,良久,缓缓从怀里拿出一个脱色打皱的香囊,拇指轻轻摩挲着,温柔地仿佛讲了半生的故事。“你那时把别的姑娘的香囊偷偷塞进我怀里,看我出丑,我就也偷了你的香囊,想把它塞进哪个公子袖子里,没想到我却留着它,留了这么久……”他的模样突然让我想到很多年前的时光,好像我与他,也算有着两小无猜的日子。就像某年初雪之日他的生辰,我站在魏府大门的台阶下冲他笑,看着他目光逐渐柔软,或是最初那个上元佳节,他站在灯火阑珊的易河边,笑得温柔。我突然很想问他,举荐兄长的事情,是有难言之隐,还是有无可奈何?但我终究还是没有说些什么,只是静静看着他,看了许久许久,最后一步步朝外走去,身后那扇门,就像我们之间错过的遥远时光,缓缓合上。第二日一早,长欢红着眼眶来给我传话,二爷走了。身子已经凉了,约是夜半走的。我比自己想象得要冷静太多,有条不紊地安排了丧礼各项事宜,但自始至终,我都没敢去见他最后一面。只是临盖棺前,我还是去见了他。他的鬓发被梳得整整齐齐,身上玄色官袍熨帖平整,如若每个他衣冠楚楚上朝的日子。我突然想起来很多年前我的大婚之夜,他站在屏风外局促不安地望着我,好像我那时本不该掀开盖头的,喜婆说不吉利,但我忘了。我望着他寂静的面庞,扯起嘴角笑了笑。当真是不吉利啊。有一滴泪从腮旁流下,也仅仅只有一滴眼泪。几日后,父亲过来看我,待他临走之时,我突然站起身问道:“父亲,如果那时不是魏涉举荐,皇上还会派魏延去打那场仗吗?”他闻言停住脚步,缓缓转身看向我,眸色寂凉沉重。自母亲过世那时起,我已经多年未在他身上看到这种眼神了。“魏延曾受晋王重用手握兵权,且魏家军只听令于他,皇上即便是除他兵权,到底也是怕养虎为患。魏延一直都知道,只有他不在了,才能真正保住魏家,所以,原本他是让我上折力荐他攻打蛮夷南方边境……”父亲说着便从袖口掏出一份奏折,“他说,若是由我将他推向深渊,或许就能消弭圣上对魏卓两家联姻的忌惮,以他一人之命,保全魏卓两家。”我只觉得呼吸一窒,往后退了两步,努力撑住开始支离破碎的仇怨,苦涩地笑了起来:“不可能,那为何是魏涉……”有寒风吹过堂厅,我的衣袍被吹得烈烈作响。父亲转过身不再看我,发髻在寒风中凌乱,苍老的声音嘶哑干涩:“阿尧,朝堂事事终究不是你想的那般简单,魏涉举荐兄长,担下了世人煮豆燃萁的骂名,担下了你的仇视憎恨。那你试想,若举荐魏延的人是我呢?”他沉默良久,长叹了一口气:“我想,魏涉大约是不想让你恨我吧。”说完他便朝门外一步一步走远,我望着他逆光远去的沧桑背影,慢慢瘫坐在地上。我想过这么多恩怨情仇,想过这么多纠葛缘由,可到头来,这根本就是既定的命运,无能为力,万念俱灰。昏黄霞光逐渐黯淡,响起淅淅沥沥的雨声。不知过了多久,屋内被一盏孤灯照亮,我听到长欢惊呼一声,匆忙跑来搀我起身:“夫人,这么冷的天,怎么坐在地上?”可我只觉得心里冷得厉害,抬头看向门外沉寂的雨幕,一点点闭上了双眼。 监制:飞酱 主播:呆头小树妖 编辑:Appie/阿菁/五六七 ??点击“阅读全文”,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fulonggana.com/flghxcf/7599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