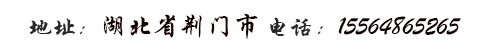从侯宝林梁左到郭德纲娱乐至死的中国相声
| 白巅疯 http://pf.39.net/bdfyy/bdflx/140809/4445035.html医院订阅哦!国庆期间,碰巧在电视上看到朱迅主持的一档节目,一票数得着的相声演员,有“宝”字辈的老先生,也有相声新秀,算是相声界的顶尖聚会。双簧、贯口都来了一轮,也有个别包袱不错,但整体听下来,总有一种隔着袜子被挠脚心的感觉,不舒服。虽然郭德纲嘴上不饶人,经常骂同行,无论人们怎样评价郭德纲,不得不承认的是,德云社这二十年,把相声这个曾经辉煌却日益僵化的曲艺形式带火了。没让相声变成这种为政治服务的“三下乡”节目。郭德纲有个著名的相声段子叫《五十年相声怪现状》,从老北京天桥艺人说起,相声的崛起靠的是“平地抠饼、对面拿贼”的本事,叫得下好,要得来钱,否则就得饿肚子。关于解放前天桥的曲艺生态,郭德纲说得没错,但是细究起来,新中国成立后,中国相声也经历了几次起落,但是这种兴衰,就要放在政治曲线中来讨论了。回顾一下相声的发展,“八德”的年代我们没赶上,更别提穷不怕老先生。解放后崛起的相声,主要是“宝”字辈的,侯宝林、刘宝瑞、郭全宝,当然天津还有辈分更高的马三立先生。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段子保留得最多,这就要感谢毛主席,他老人家爱听侯宝林。从年起,侯宝林就给毛主席说相声,据说有一次毛主席听《关公战秦琼》,说完之后让侯宝林和郭启儒再说一遍,俩人没辙,又重新说了一遍,毛主席还是乐得笑逐颜开。有了毛的支持,侯宝林得以在建国后施展才华。虽然在体制内,但侯宝林不愧是相声大师,巧妙地利用“新旧”社会的区分,将相声的讽喻功能放到旧社会,既能抖包袱,还足够辛辣、真实。建国不久,侯宝林先生说过一个《八大改行》,说的是光绪皇帝驾崩,国人服丧百日,那种国丧肃杀之下的教条和荒诞,比如说有一段是这样的:甲:出门不行。我听我大爷说过,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。乙:鼻子是红的?甲:出去买东西去啦。看街的过来,“啪”!就给一鞭子。赶紧站住了,“请大人安!”“你怎么回事儿?”乙: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儿?甲:“没事呀,我买东西。”“不知道国服吗?”“知道!您看,没剃头哇。”“没问你那个,这鼻子什么色儿?”“鼻子是红了点儿,天生长的,不是现弄的。”“不让出门儿。”“不让出门儿不行啊!我妈病着,没人买东西啊!”“要出门来也行啊,把鼻子染蓝了!”这种通过讽刺旧社会达到政治正确,同时保留包袱里的刺,指向的是一切权力带来的荒谬禁锢,也就使文本有了共性。还有《关公战秦琼》,讽刺那种啥都不懂,仗着权力乱指挥的人。侯宝林先生搬上电视,还给毛主席说,遂发扬光大。据说这段成书于上世纪30年代,本来说的是张宗昌,后来侯宝林改编,因为当时正在批判梁漱溟,有“韩复榘用枪杆子杀人,梁漱溟笔杆子杀人”,于是侯宝林将主人公改成了韩复渠的父亲,“大将生来胆气豪,腰横秋水雁翎刀。我本唐朝一名将,不知何事打汉朝!”除了侯宝林,还有像刘宝瑞的单口《珍珠翡翠白玉汤》、马三立的《开粥厂》等等,都是经典作品。都把传统相声的技巧用到极致,还利用了新旧社会的时代转换,巧妙地将讽刺转化到“旧社会”,但指向的,往往是普世的人性。但是,相声不免被政治工具化,口号宣传式的“群口”如《帝国主义纸老虎》,歌颂新人新事的《新诗风》等等,到文革时期还出现化妆相声等等,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地方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,这个中国思想的“黄金时代”,禁锢被打破,人们从极权和狂热中苏醒过来,进入一个自由奔放的时期。相声作品的批判性,也在社会变迁的裂隙中,寻找到更多的讽刺对象。首先是马季在年春晚的单口相声《宇宙牌香烟》,据说这个节目也让当时的导演顶了巨大的压力,但还是坚持上了,将讽刺矛头指向了商品经济冲击下的“假冒伪劣”,到年,马季推出里程碑式的群口相声《五官争功》,在所谓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的口号下,在平均主义像市场经济转化时,个体、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,通过“五官”的隐喻展示出来,《五官争功》甚至发表在当时的《人民文学》上。看一段精彩的文字:嘴巴:脑袋,我对你有意见。脑袋:对我有意见?嘴巴:嘿嘿。脑袋:怎么啦?嘴巴: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在最下边?脑袋:是啊,当初它就那么设计来着。嘴巴:你得把我的位置往上调。脑袋:怎么调法?嘴巴: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。脑袋:这嘴长到这儿来?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呀?嘴巴:我得最高啊!鼻子:脑袋:!我对您有意见。脑袋:你有什么意见?鼻子: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,我得站最高峰。脑袋:好!他也长到这地方来?眼睛:脑袋:!我高瞻远瞩,我请求上调。脑袋:你也上来啦!耳朵:脑袋:!我耳朵也得必须长你脑瓜顶上。脑袋:耳朵也长……我成兔爷啦!同样经典的还有马季的《吹牛》等等,如果说他相声的“刺”指向了社会底层现实,另一个作者,则将相声的“刺”更大胆的指向了制度变迁,在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,也开创了中国相声的“黄金时代”。这个人就是梁左。没错,就是那个写《我爱我家》的梁左。回望他在相声领域的创作,绝对是开创性的,姜昆的走红,一部分是因为马季的培养和提携,另一部分原因就是得到梁左的好本子。同样是在年,马季演出《五官争功》,姜昆和唐杰忠演出了梁左编写的《虎口遐想》,用今年的表述,就是一个“屌丝青年”掉进老虎笼子里的故事,还有心思想着找对象,还要各种逗贫,例如:姜:算了算了,你们都走!你们出动物园,找电视台,让他们派个摄制组来,拍一拍等会儿老虎怎么吃我!”唐:拍这个干吗呀!姜: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,卖给外国人换点儿外汇,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“七五”计划做点贡献了。《虎口遐想》的文本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画面感,姜昆的出色表演也营造出一种小人物喜剧的典型氛围。比如刚出来就想着把姑娘的裙带子还给人家,还能想到上边的体香……还有梁左创作、姜昆演绎的经典《电梯奇遇》,姜昆去办事,结果被卡在老旧的电梯里,于是人事科、宣传科、伙食科、卫生防疫科,各种人浮于事的奇葩经历,并且带有强烈的时代特点。看宣传科长怎么说:姜:“这是个难题喽!对你个人来说,把你关在里面,这是一件坏事;可是对于全局来说,对于我们整个革命事业来说……也没有什么好处是吧?所以,这就是新大楼和老电梯新旧体制交换时期所产生的一种矛盾,目前你关在里边,暂时还不适应,对不对?”唐:难受着哪!姜:“那要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呢?”唐:那就……更受不了啦!姜:“所以,你要加强学习,丰富自己,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……”唐:他走得出去吗?姜:“给一点儿鼓励嘛!我们的口号是:大干苦干天,第一委度开门红……这个门好像开不开是吧?那我们的口号是:高高兴兴上班来,平平安安回家去……家也回不去了是吧?那我们的口号是……”各种表达方式的年代感背后,尤其是“相当长的历史时期”、“大干苦干天,第一委度开门红”,都是从政治表述中获得的灵感。再看人事科长怎么说:姜:“效率嘛,说办就办!我这就给你们单位去个商调函,把你的关系办过来,你就算在电梯里头上班,白天算你出勤,晚上算你值班,想睡你就睡会儿,睡不着你帮着抓抓坏人什么的,你们大伙儿说我这主意怎么样?”唐:够馊的!他在里头关着,能抓坏人吗?姜:“那阶级敌人在外头转悠,你就在里头干看着?”唐:可不干看着吗?在阶级斗争的年代,单位、关系这样的集体管理,是不是也让人觉得陌生又熟悉?里边的大量的包袱从政治中来,譬如研究决定让姜昆在电梯里享受“科级待遇”,还赋予了“孤胆英雄”的称号,可以享受相应的伙食标准……除了《电梯奇遇》,梁左还创作了把冯巩、牛群捧红的《小偷公司》,最后那一句,“民警同志,官僚主义害死人的!”瞬间点破了主旨。看看小偷公司的组织架构,让人喷饭,又很黑色:冯: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?牛:哎,你这话的:”火车跑得快,人凭车头带。干部带了头,小偷有劲头,小偷没领导,肯定偷不好,不是偷不了,就是跑不了。”冯:那你们都有什么干部呀?牛:那干部多了,一个总经理,四十八个副经理。冯:四十八个人儿呀?牛:各管一摊呀。冯:都管什么呀?牛:有管行政的,有管组织的,有管宣传的,有管后勤的,有管计划生育的……臃肿的机构、空洞的口号,这就是《小偷公司》和《电梯奇遇》折射出的政治生态,也让这些作品成为像手术刀一样的存在。其实,同时期乃至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前,小品也一定程度上有这样的痕迹,赵本山的《牛大叔提干》、陈佩斯和朱时茂的《警察与小偷》,都是语言类的难以复制的经典之作。郭德纲在《相声五十年之怪现状》中极力抨击的是“相声一定要有教育意义”,从个人恩怨讲,是针对要求取缔小剧场的姜昆,从相声的表演方式上讲,则描述出相声在年前后的尴尬。完全脱离小剧场,基本上没有了演员和观众的互动性;审查禁区越来越多,讽刺空间变得越来越小,所谓“理不歪笑不来”,但讲出“歪理”的,大多是与日常生活既联系又冲突的可笑之人。如侯宝林先生《关公战秦琼》里的韩老爷子、刘宝瑞《珍珠翡翠白玉汤》里的朱元璋、马季《宇宙牌香烟》里的推销员、《电梯奇遇》和《小偷公司》里的一帮奇葩官僚。在德云社的前十年,郭德纲从两个方面展示出才华,一个是对传统曲艺的改编和传承,譬如说发扬相声本门唱太平歌词,还有结合评书的长篇单口《济公传》《丑娘娘》《张广泰》等等,都很见功力,但这种见功力的表演,大多只能维持非常专业的观众。在传统相声的传承上,郭德纲的前辈们都有卓越的努力,马志明的《大保镖》、苏文茂的《苏批三国》、侯耀文的《口吐莲花》、李金斗的《捉放曹》等。但真正要让相声适应电视传媒时代的大众,仍然要寻找当代语境中的讽刺包袱,才能触及流行的痛点。如侯宝林和刘宝瑞讽刺旧社会,如马季、梁左经典作品的时代性,郭德纲在这一点上也找到了出口,著名的“我”字和“你”字系列就是代表,诸如《你要幸福》《我是黑社会》,都将焦点集中在当代社会的小人物——所谓“屌丝”。屌丝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收入阶层,也是一种精神状态,既是当下人的一种自嘲,也是一种来自底层心理的玩世不恭。郭德纲在早期的这两个系列中,将屌丝的状态和流行元素嫁接,加上传统相声的伦理哏,非常容易激发出舞台效果,譬如《我是黑社会》讲的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想当黑社会闹出的笑话,有一段父子俩的对话:郭:老头一边儿吃,我就烦他这个。破嘴,得得得得得,你也干点儿正事儿,你说你混成这样一天到晚的连个正形都没有,你瞧瞧人家,开车的买大楼房的,你看看你,你一无所有,你脚下的地在抖,你身边的水在流,你的手在颤抖,心中的泪在流。于:你爸爸姓崔?郭:你爸爸叫健!讨厌,我爸爸说我呢。于:说你别唱歌词啊。郭:(转向于谦)听话,爸爸说你都是为了你好。于:你冲那边儿说去!郭:(转向外边)我说爸爸您别生气啊。于:呵,这时候转过来吧!郭德纲很善于在表演情境中结合网络段子、歌曲等流行元素,加上于谦这样优秀的捧哏,会不动声色的完成跳进跳出,包袱瞬间抖出来,出其不意,效果奇佳。在文学性上,郭德纲的这两个系列作品虽然不如梁左,但也塑造出契合当下社会心理的小人物形象,加上对传统相声包袱技巧的娴熟使用,节奏感掌握得好,包袱就抖得响。随着德云社规模的扩大,郭德纲更多只在封箱、开箱的重要活动中演出,也都集中在北展剧场,数千人同时听。郭德纲无疑很聪明,他逐渐放弃了剧本的文学性,反而更多依靠诸如“于老师三大爱好”这样不断重复累积的包袱效果,更多伦理哏是使用,当了当于谦的“爸爸”、和于谦的“媳妇”眉来眼去,譬如有这样的包袱:于谦的“媳妇”抱怨郭德纲,“你身体不如从前了啊。”又或者是于谦“媳妇”碰洒了郭德纲的面,说道“我赔(陪)你一碗(晚)便是。”或者进一步带有屎尿屁暗示的笑料,“我们大小便认识,如今大变样。”面对几千人的大剧场,这样的段子显然能更快让大家笑。仅凭这一点,就比央视节目中那些让人尴尬的演员强。但从相声发展的趋势上看,郭德纲的相声在文学性上正在逐步削弱,讽刺更多变成了搞笑,回味变得越来越弱。这一点倒是跟娱乐至死的当代社会很契合,80年代的自由空气从此不再,梁左式的辛辣再无空间,郭德纲巧妙地找到了相声完全娱乐化的道路,他早期优秀的作品如“你”“我”这些系列,甚至包括传统的长篇单口也不再说,却反复使用跟于谦的身份错位,用最保险的段子来逗人乐。郭德纲正在回到真正意义上的“传统相声”,即天桥文化熏染出来的本事,据说有个王爷让一个相声演员不说话逗大家乐,那哥们儿跑到台上一下把裤子脱了,瞬间哄堂大笑。郭德纲将这种搞笑的节奏感和技巧掌握得炉火纯青,但也意味着逐渐放弃了侯宝林、刘宝瑞、马季、梁左,甚至包括他早期作品中那种不断传承和创新的,以讽刺为基础、丰富的细节和完整故事构成的文本。他转向了碎片化的表演形式,并发扬光大。这是他的选择,也是大众传播时代的需要。郭德纲重新激活了相声的大众传播,但是这个日益凋敝的土壤和肃杀的空气里,他最终只能走和梁左不同的娱乐化道路。他广收门徒、用商业表演和舞台承接着传统相声的手法,我们只被允许二人转式的快乐,相声里讽刺性的幽默基因,恐怕随着梁左和马季的逝去,以及日益严格的控制,与相声渐行渐远,最终无法摆脱政治发展曲线影响下的命运。中国相声界是个江湖,里边的是非恩怨咱不管,也无法讨论。只是从社会环境上看相声的发展趋势,郭德纲式的搞笑,梁左式的讽喻,我无意对比优劣,这是不同的艺术手法。但是当前的空气中,已经无法产生梁左,相声就沿着被迫选择的娱乐化道路,硬着头皮走下去,《小偷公司》和《电梯奇遇》里那些自由的空气,已经一去不返了。非典型佛教徒针砭时弊不舍慈悲理性思考不许骂人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fulonggana.com/flghxcf/4011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中医诊疗51临证特色五治疗血证的经验
- 下一篇文章: 转基因中药必须知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