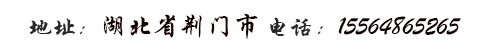母亲对保德家乡的回忆
|
人老了爱回忆过去,我的94岁的母亲更不例外。她28岁离开保德家乡,迄今已经几十年了,晚年时候特别爱讲家乡的故事,我总是耐着性子听她唠叨。一天,母亲让我把她的故事整理成文,在山西日报社离退休处办得一份刊物上发表,我遵命动笔。文章发表后,老干部们说有点教育意义。 母亲的家乡在黄河边上,那是保德县一个极其贫瘠的小山村。而保德县本身就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县之一。旧社会生活在保德县的人,看惯了沟壑纵横的黄土地,听惯了地瘠民贫的走西口,旧社会流行的那首歌谣“河曲保德州,十年九不收,男人走口外,女人挽苦菜”就是母亲家乡的生动写照。 保德县名称出自:“民保于城,城保于德。”这句话源自《左传?哀公七年》。大意是百姓由城邑来保护,城邑由德行来保护,其核心指的是传统“德”中的“信”和“仁”。 母亲居住的桥头镇郝家里村在半山腰上,听母亲说,本来是叫合家里村,早年有三户逃荒的人搬到了这里,一户姓李,一户姓白,一户姓康,三家合成一个村,故起名合家里村。不知怎么的,后来叫成了郝家里。后来,全村发展到四十多户人家,都是依山而居,住着土窑。土窑有土窑的好处,居窑者夏不畏酷暑,冬不惧严寒,窑里始终是冬暖夏凉,唯一的缺点是光线不足。家境好点的人家炕面是石头炕,用红泥和胭脂刷红,主人每天用麻油擦拭,久而久之,红油铮亮,俗称红油炕,农民们多在这种炕上擀长豆面。饭食通常是:早晨糜子面窝窝呵(蒸)山药,豆面拌汤或小米稀饭。午饭多为捞饭或杂面,晚饭多为和子饭或豌豆稀粥。一年四季,酸菜下饭。 全村以白姓为主,因为没有路,也没有交通工具,出门就爬山,到乡镇赶集就得攀岩,到了夜里根本无法出门。全村人的所有生活用品都得靠人扛肩挑或者背。你看吧,出门的人不是背着粮食,就是背着炭和柴禾,反正没有人走空。久而久之,村里的人驼背、罗圈腿的人很多,因为走山路的缘故,八字脚的人也多,我的父亲就是如此。村里每年都有因为行路难摔断腿的,也有摔下悬崖跌死的人和牲口。因为土地贫瘠、地少人多,一年到头,人们都在为了填饱肚子拼命劳作着。这里的孩子没有快乐的童年,只有劳动的童年,大人干重活,小孩干轻活。母亲很小的时候,牛在前面耕地,她们小孩子跟在牛屁股后面,提个小篮子,不是往地里撒粪就是点豆、种山药蛋片和其它杂粮籽。因为人小,牛走得快,一会就把她们啦到后面。夏天,大人锄地,她们担着饭罐子和干粮,要负责给送饭。庄稼长得高,风一刮,就和狼吼得声音一样,吓得小孩子们跑得飞快。秋天,大人刨下山药蛋后,撒得遍地都是,小孩子们负责把山药蛋从蔓子上摘下来,拢成堆堆。中午休息时回不了家,她们就拢上山药蛋蔓子烤上几个山药蛋,经常是半生不熟就吃到肚子里了。天黑得看不见了,人们才能收工背着山药蛋回家。大人多背,小孩少背,谁也不能空手。走在山路上黑灯瞎火,连走带摔,到家时浑身上下全是土,又饿又乏。各种豆子收获后,大人把蔓子背回来,小孩子们坐在油灯底下,把各种豆角子从蔓子上摘下来,经常是边干边打盹。 母亲稍大一些,就和爹妈一起下地,春种、锄地、秋收、担水、推磨、喂牲口。母亲的家乡缺水,担一担水,要走几里山路,下到很深的沟里,不是下坡就是上坡。母亲的家里喂着一群鸡、一头牛、一头驴,还雇着个半哑子放着一群羊,这么多的嘴要吃,哪有个空闲时间!最怕的是母羊冬天黑夜下羔子,母亲和爹妈举着个小麻油灯,每人披着件烂棉袄,一直守在羊圈里等着,否则不是冻死小羊羔,就是大羊踩死小羊羔。母羊生产完,还得给备好一大锅稠米汤和一些精饲料,好让母羊有奶。刚过完年,牛还没有下地送粪,母亲就要赶着牛把一家人吃的面尽可能多得磨下。母亲整天钻在磨房里,牛在前面拉磨,她在牛后面填磨眼、扫磨盘、罗面等。即使牛休息,她也得赶紧往家里搬磨好的米面。那时家家都是这样。春种秋收,人吃牛喂,全靠两只手刨闹。 母亲的父亲会针灸,会开草药,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,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土中医,加上他经常义诊,所以深受家乡人的欢迎。当然,他也只能治疗一些简单的病,但是也为村里人的健康,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母亲记得他用的针刺疗法,感冒头痛就是印堂放血;急性肠胃炎就是尺泽放血;小儿疳积是十宣放血。开的单方主要是:伏龙肝止吐;红糖水止泻;独头蒜止痢;甘草一味治淋涩;苦豆根治咽部肿痛,等等。 作者简介:康小明,山西作家协会会员,曾任某媒体主编,高级记者出版散文集《编委楼纪事》。自由撰稿人 赞赏 人赞赏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fulonggana.com/flgjbzl/773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2018中综考研复习满满的干货系列十六
- 下一篇文章: 每周一来海王星辰学煲一款靓汤本周夏至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