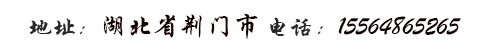伏龙肝
|
父亲的形象是在母亲通奸的私情败露那天在小文心目中彻底坍塌的。 当父亲举着那个独眼男人的皮鞋要打他时,袒露着胸脯的母亲往那男人旁边一站,像不少影片中作战场鼓动工作的女宣传队员一样说:让他打!让他打! 独眼男人受了鼓励,本来软塌了的腰杆弹簧样又绷直了。 父亲犹豫的当口,母亲竖着眉,奚落着父亲说,郭伟,你认为你是啥英雄好汉?你是战场上一个逃兵! 父亲听到母亲这句话,高举的手受了电击一样垂了下来,手中的皮鞋橡皮鱼一样沉闷着落在地板上。独眼男人趁机穿鞋溜走了。 这时,小文就有点怕,他不安地揣测:独眼男人一溜,父亲对那男人的仇恨将转为对母亲的仇恨。看吧,父亲的拳头会像拳击手打沙袋一样打在母亲白腻腻的身上。如真这样,不到万不得已,他不得不制止父亲,掩护母亲。 这一刻父亲的形象的确可怕,他咬牙切齿地盯着母亲,拳头也越握越紧。母亲对视着他,不紧不慢地扣她的上衣扣子。父亲进攻的企图被母亲的目光粉碎,他攥紧的手掌伸展叉巴开来,蹲下身子一下捧住了凄苦的脸。 小文的期待化为泡影,他心中替父亲不平,也恨父亲窝囊。这时,一直提在他手中的一条活鱼一个打挺跳到了地上。父亲发现了儿子,霍地站起来,紫涨着脸对小文吼了声:滚! 小文怎么也没想到父亲会对自己发威,他愣怔了一下。 这时,父亲更厉害地对他吼了声:滚! 小文的头一阵昏眩。委屈的泪水一下涌满眼窝,他哭着冲出房子。 郭伟是在新城兵站掉队的。 那天上午10点,郭伟和他的战友在新城兵站登上了开往前线的列车。他清点过人数,检查完携带的武器装备,刚坐在背包上休息,排长走过来说,三班副,上街买10根捕俘绳。 这……郭伟担心时间来不及。 排长戴手表的右腕一翻说,离发车还有五十多分钟。 生活往往以轻松的方式给人开严酷的玩笑。 郭伟买到绳子,拼命地挤上了返回的公共汽车。红灯、红灯,怎么老遇上红灯。他想到了下车,可没下。下了车,跑几步,汽车又撵上了你,你就会对自己的小聪明后悔不迭。 汽车一到站,他急溜蹦星地赶到兵站。正好,离发车还有十多分钟。他记得清楚,他坐的那节闷罐车厢正对着兵站的大门。车厢的铁门敞开着。他一个箭步跳上去。糟!车厢里全部是陌生的面孔。原来,这是另一军列。 十万火急啊,郭伟不顾兵站管理人员的呵斥,一连钻过停站的四列火车。快!只要能跳上末节车厢……就在这时,列车向他顽皮地呜一声长啸,接着,朝天吐出几大口白气,切格切格嬉笑着向前跑了。 郭伟掉队的事件被部队留守的保卫科干部查了两天,最终认为他临阵脱逃证据不足,给他一个警告处分,然后让他随后续部队上了前线。 到了前线没几天,郭伟奉命执行捕俘侦察任务。出岳丛林地带,没有路,需要斩荆披棘排雷,半天才走了平原四五十分钟就可走完的路,开辟通道越来越艰难了,郭伟在砍一丛荆棘时,感到背上的冲锋枪被什么绊了一下。郭伟一边抹汗,一边顺手拉了下枪背带。这时,奇怪的事情发生了,他听到消音冲锋枪子弹出膛的类似放屁大的一声响。郭伟一愣神,感到臀部一阵剧烈的灼痛,他下意识地用手去摸,黏腥的鲜血冒着沫儿从他指逢间涌出来。受伤了。郭伟明白了这一事实,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,拉过枪管一看,他吃惊地张大嘴巴:怎么会是自己的枪?怎么会是自己的枪? 后边的战友听到了枪声很快赶来。一个战友问:敌人在哪个方向? 郭伟在这一刻竟幻想他的伤真是敌方打来的,他稀里糊涂地摇了摇头。 排长看了看郭伟的枪口和他被子弹灼焦烧糊了的臀部裤子,一切都明白了。枪伤,近距离枪伤。一出样板戏里那个叛徒开枪打伤自己的场景在排长脑际凸现出来。 排长啄木鸟一样深?的眼光在郭伟因疼痛而变形的脸上扫一扫,这凶狠的目光一会儿转为鄙夷,他挥一下手,冷漠地对两个战士说,把他抬下去吧。 小文从懂事时就看出,母亲对父亲的冷漠,是心里的冷漠;母亲对父亲的鄙视,是骨子里的鄙视。在小文的印象中,母亲很少与父亲在街上同行,即使一起上街,也是一前一后地走。母亲在前时,后边的父亲像跟着贵夫人的一只狗;父亲在前时,后边的母亲像农夫赶着一头驯服的牛。平时在家中,母亲很少跟父亲说话,父亲的话母亲听了要是感到不顺耳,母亲便像放飞一窝小马蜂一样,一字一句都带着毒刺儿蜇得父亲够呛。 那天,小文翻柜子时,在柜底发现一个红盒子,他打开一看,里面是一枚军功章,他问父亲:这是您得的吗? 是的。 爸爸立的是几等功? 三等功。 小文没想到父亲身上还有这个美丽的光环,可惜,要是功再高点,母亲或许就不那么看不起父亲了。他不由得说,爸爸要立个四等功,五等功就好了。 郭伟笑了,说,三等功是最低的,哪有四等功,五等功。一等功才是最大的功哩。 小文也为自己的无知笑了,他问,爸立的是战功吗? 郭伟摇摇头说,是训练成绩好得的。 小文知道了父亲枪法很准,一溜儿排十个酒瓶,将十个乒乓球放在每个瓶嘴上,父亲占在30米之外,手枪一甩,啪啪啪……十发子弹出膛,十个乒乓球像十窝白蝶炸飞起来,而十个酒瓶完好无损。凭这硬招,父亲曾作为大军区的惟一代表,参加了全军通用步枪射击比赛,并取得优异在绩,这功勋章就是那时得的。 在小文为父亲的好枪法骄傲时,父亲给小文讲了一个不会打枪的兵的笑话。父亲说,那年进行手枪射击训练,月亮门大的山洞前竖着个胸环靶,一个姓吴的兵,站在射击位置,他举着的手枪像个啄米鸡,一扣扳机,鸡脖子就下栽。打出的子弹,不要说上靶,月亮门都没接住他的“花生米”,子弹都噗噗叫着,钻进他脚前两米多远的黄土里了。 听到这里,小文开心地笑了。 在一边的母亲这时哼了一声,乜斜着父亲问,那姓吴的兵,子弹打没打到自己? 父亲没有听明白母亲的揶揄,说,好险哩,再近,就打到自个的脚面上了。 母亲说,我想,他小吴再笨,子弹也不会打到自己的屁股蛋子上。 那时,小文还听不出这话的刀锋有多么犀利,内涵有多么丰富。父亲却下子涨红了脸。刚才还兴致勃勃的父亲一下就成只瘟鸡,耷拉着头,踱到房外边去了。 郭伟受伤后,连长、指导员分别和他谈话说,自伤可是政治事故,弄不好会被判刑的。连队干部也要跟着你砸锅。上级要调查,你要一口咬定是枪走火。 郭伟听了这话十分委屈和愤懑:我本来就是意外走火,为什么还让我一口咬定,为什么?那天走火的原因一定是这样的:他感到枪背得不舒服去拉枪背带时,枪板机挂住了荆棘背囊带或子弹带,枪就响了……但郭伟没有申辩,他知道,有些事会像写大字对某一笔不满意再用笔去描一样,描不好,反而越描越糟。郭伟还想,只要再上战场,就有“验明正身”的机会…… 人,对于自己,是个雕塑家,时刻都在镂刻自身。而你在旁人眼中,则是一个裸体模特儿,任凭色人等,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你、审视你。在养伤那几日,郭伟感到自个就是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的模特儿。 韦大伯,你的鸡下软蛋了。同班战士小姜喊。 房东大伯听到喊声,走出木屋,一看鸡窝说,小姜又逗我哩。 不是软蛋,也是滑蛋。小姜白郭伟一眼说。 郭伟的心被噗地捅了一刀。 在这个时候,郭伟明白,对天一个有脊梁骨的人,最难以忍受的屈辱莫过于让人说是怕死鬼了。他想,你让人认清你,那么,你就得庄严地献出自身。郭伟比任何时候都渴望战场,渴望牺牲。 伤好后,他三次写血书要求参战。 连队首长让他执行的第一次任务是给前方设伏侦察的战友送给养。他走到一个山脚密林里时,感到脚下踩着了异样的东西。地雷!他一惊,但一时的恐惧马上被一阵快意的悸动代替了。我要死了。我是死在战场的。我是被敌方的地雷炸死的。他的嘴角溢出一丝甜蜜的微笑。他等待着那一声或清脆,或沉闷的爆响;等待着巨大的气浪把他托上天,掷下地。接着自己的血如喷泉一样流,像一首诗里写的:染红一丛,碧绿的野草,浇灌几簇,含苞待放的杜鹃……可是,好大一会儿,地雷没有爆响。他疑惑地从腐烂的树叶里提起那颗菠萝形地雷,他的目光僵住了:地雷的保险孔里插了根大头针,击针被固定了。原来,这是颗被谁排过的雷。他失望极了。这时,他听到一阵脚踩树叶的沙沙声,后边的战友跟上来了。郭伟像一个正在作案的罪犯一样,慌忙丢掉那颗菠萝形地雷,离开了这个令他激动、令他遗憾的地方。 那年,小文坐父亲开的出租车去城北郊的姥姥家,返回时,父亲的一个战友搭上了车,这个白白胖胖的叔叔上了车问: 郭伟,咱们战友元旦成立“战友联谊会”,你知道不知道? 还不知道。父亲答。 白胖叔叔说,这些年,兴这个。社会上同学联谊会、战友联谊会多得很。他们哪是什么战友呀?咱们那年的兵,名副其实的“一条战壕里的战友”,是得联谊联谊。战友心扭结着心,筋疙瘩着筋,是攀山的路,过河的桥哩。 白胖叔叔下车后,父亲显出平常少有的兴奋,他给小文讲了在新兵连的一个故事。 新兵连的营房坐落在一个山高林密、野兽出没的山坡上。新兵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,夜间站岗,免不了有些害怕。有个新兵那天夜间站岗时,天阴得像浸了墨,一会儿又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。这个新兵心里一阵阵吃紧,总觉得雷电中的树像厉鬼一样呼啸着一排排向他扑来。他害怕得四处张望。忽然,他看到一个蘑菇形的影子一跳一跳从山道向他这个方向窜来。妈呀,这是啥大头鬼啊!新兵吓得心都跳了出来。他惊叫着,扔了枪,就往营房跑。 这新兵跑到营房,结结巴巴地将他看到的情景向其他新兵讲了。一个胆大的新兵站出来说,咱们去看看它是个啥鬼。 胆大的新兵带着几个人走到营房门口,看到那个黑大头鬼进了炊事班的厨房。胆大的新兵跟进去,只见厨房里站着水淋淋的炊事班长,他身边放着一口直径一米多的铁锅。原来,炊事班长去集镇买锅,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大雨,他灵机一动,将锅扣在头上当雨伞打着。 父亲讲过,那个胆小的兵就是刚才你那位白胖的叔叔。父亲说完,停了会儿,有点买关子似地问儿子:小文,你知那个胆大的兵是谁? 小文看父亲的神态已断定那胆大的是谁了,答,是爸爸。 郭伟笑了,笑得十分开心:好小子,真聪明。 元旦快到了,父亲还没接到战友联谊会的通知,就找电话号码拨通了那个白胖战友家的电话,白胖战友说,怎么,你还没得到通知?你再等等,这活动是老胡发起的,他会安排人具体通知你的。 第二天,父亲提前收了车,回到家就问小文和妻子,有没有人找他或来过电话。当知道没有时,他失望地闷着头一个劲儿抽烟。 父亲元旦前几天都提前收车,可总没有让他参加战友联谊会的通知。 元旦那天,他破例没有出车,直到上午十点,仍然没有任何消息,父亲彻底失望了。 这天,父亲像得了重病一样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睡了整整一天。 打这一年开始,父亲的战友每年元旦都联谊一次,每次都没有人通知父亲。父亲这一天都没有心思出车,都要躺在床上睡一天觉。 郭伟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,别的连队要接防他所在侦察连的防区了。他还没有用行动洗刷自己身上所蒙受的尘垢。郭伟心中有种难以表达的依恋阵地的痛若。 机遇就在他最失望的时候降临了。近两天,对面敌军增加了一个活动炮兵群,无规律地向我方阵地和边境居民区发起炮击。上级决定郭伟所在连实施渗透侦察,摸清故情。连长或许是想给郭伟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,便让他参加了侦察小组。 在潜伏时,郭伟感到双腿针刺般的疼痛,提起裤管一看,几十条旱蚂蟥扎在他腿肚上吮着血,它们就像一片钻出黑红色地皮的墨绿豆牙儿。郭伟不禁一阵肉麻胃翻,他挥起巴掌,正要严惩它们,不知是突然想起制服它们不能拍打,还是其他什么缘故,他举起的巴掌慢慢放下了,绷紧的脸也舒展开来。他竟像欣赏稀世珍玩一样,脸上溢满了笑,放着异彩的目光爱抚着蚂蟥说,小魔鬼们,快快吮吧,可别饿着肚子出来,我郭伟喂饱你们一回。 不大一会儿,一个旱蚂蟥的吸盘吹了气一样膨胀起来。它们过足了血瘾,陆续从他的皮囊脉管中退出身。郭伟平日洗澡搓身上的泥垢一样,用手一下一下将它们往一起赶,然后,将它们一伙儿拂下身…… 小文不明白,父亲为什么那么怕母亲,母亲为什么在父亲面前那么冷,那么凶。小文曾这样猜测:恐怕父亲有什么短处在母亲手里。什么短处呢?这是小文心中揣了很久的一个谜。 为了解开这个谜,那天,小文大了胆 问了母亲。母亲搂着他哭了。 母亲说了父亲战场上败节没骨的事。 母亲说,因他贪生怕死,他的另一个姓王的战友接替了他去开辟通道。小王一会儿就触雷牺牲了。 母亲泪花纷飞地说,小王是我的同学。我们俩毕业后就订了终生。 母亲拿给小文一张照片。 那是一个很英俊的男人。 母亲说,你爸还骗了我,他是在我很悲痛的时候向我求婚的。他说他会像小王一样爱我。为了尽快摆脱痛苦,我就和你爸结婚了。婚后,我才从老刘那里知道了他那丢人现眼的事。 小文听到母亲提老刘,脸上一阵发烧。 小文知道,老刘就是那个独眼男人。 母亲看出了儿子对独眼男人的厌恶,便说了句很诗意的话:老刘那颗眼,丢在战场上、种植在边境上、镶嵌在界碑上了。老刘,英雄。 小文感到好笑,小文知道,老刘是位发表过几首诗的文人。 郭伟怎么也没想到,正在他准备赴死的时候,临时担任侦察组长的副连长接到指挥所的命令:情况有变,迅速后撤。 郭伟知道这后撤意味着什么。这一后撤,可能洗清自己的机会再没有了,怕死鬼的魔影会始终笼罩着自己,甚至一辈子都挣不脱这个魔圈儿。这些天,他已深深体会到:世界上最难以下咽的苦酒,恐怕就是被人误解了。 这时,一串“悠——其其其”的怪音在雾里打着漂儿传来。 郭伟一个激灵。炮弹!炮弹!他飞速跃起,不顾一切地扑向身边的副连长。 轰的一声,炮弹爆炸了。副连长一个翻滚,挣开郭伟死死搂着他的手臂坐起来,对趴在地上的郭伟遗憾地说,立功也要讲个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 副连长对怔在那里的郭伟两手一摊说,这不尽人意的地方,这不成全人的炮弹。 郭伟像个偷腥不成反而弄翻了鱼缸的猫,神色慌乱地瞥一眼所处位置:眼前一块天然石像一堵墙一样倾斜下来,形成一个炮弹死角。这是副连长精心选择的安全界。刚才那发炮弹,是落在距他们二三十米处爆炸的。敌人打的是冷炮。 七月,小文参加高考之后的一天,父母的房间进去几只老鼠,使家中遭受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鼠害。 小文在帮父亲整理东西时,发现了被老鼠啃咬过的母亲的一个旧日记本,其中一页是记载父母月光下约会的: 郭伟挺黑的。 银辉下,像是要比较一下似的,我将奶油般白晳细嫩的裸臂靠近了他那甘蔗紫色的胳膊。 郭伟笑着说,我的皮肤不是太阳晒黑的,是月亮镀黑的。 我说,你真幽默。 他说,侦察兵夜训多。我喜欢月光。 下面的文字被老鼠咬掉了。读了这段文字,小文感到有如咀嚼橄槛般回味悠远。父母那时候的爱情还是很浪漫的,父亲也不乏幽默的智慧。可这些年,父亲活得多么沉重啊。 这时,父亲被人扼了喉管一样痛苦地哎哟了一声。 小文将目光投向父亲。 只见父亲手中抓着一套发黄的军用背包带,带子被老鼠咬嚼得一截一截的,线头在父亲手中像一大把绽开的蒲公英绒须。小文知道,这套背包带,珍藏着父亲的一个秘密:平时,大小两条背包带,一匝匝缠绕得结结实实。大小背包带结在一起像一朵盛开的花。母亲不在家了,父亲就关上门,将被子打成背包,然后,拆开。再打,再拆……一次,小文急着找一样东西,慌乱中推开父亲卧室的门,发现父亲正拿着背包带。父亲不自然地说,将近二十年没打背包了,不知路数忘没忘。 父亲有他心中的珍藏,有他个人的秘密。小文不忍心戳穿父亲的伎俩,强颜作笑地说,爸爸,您试试忘了没,儿子还没看过爸爸打背包哩。 父亲那天脸上就飞了彩。他将被子左折右叠,三下两下,小文眼花缭乱中,一个有棱有角,豆腐块般整整齐齐的背包就打成了。这时,小文的泪水,忍不住涌出眼眶,他叫声爸爸,一下扑进父亲怀里。 现在,老鼠将父亲的心中珍藏糟蹋了。小文知道父亲该有多么痛苦啊。 小文默默走到父亲眼前,从父亲手中要过那碎糟糟的背包带,扬手扔进了垃圾桶。 父亲对儿子这一行为感到不可理解和愤懑,他正想说什么,小文上前抓住他的手说,爸,以后这背包我来打。 父亲不解的目光在小文脸上扫描。 小文一字一板地说,我要当兵。 父亲惊讶地啊了声。 小文说,我高考第一志愿是军校。第二、第三志愿,还是军校! 父亲激动得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,他一下将儿子搂进怀里,眼里哗地涌出泪水。 晚上,母亲坐在小文的对面,纤着气看着小文说,小文你不能感情用事。 小文叫了声妈妈,正想再说什么,母亲打断他说,你不能马马虎虎报考军校。 小文说,我反复考虑过了。 母亲说,你不适合报军校。 小文探究地盯着母亲:我能问妈一句话吗? 母亲点点头。 我是爸爸郭伟的儿子吗? 母亲立时羞红了脸说,对妈尊重点好不好。 小文说,妈妈你回答我。 母亲哭了说,正因为你是他的儿子,妈才不让你报军校。妈担心你没有那种英雄基因,不适合当兵。 小文看着母亲,悲壮地说,我既然是郭伟的儿子,我就要当兵! 小文感到这句话不仅是说给母亲的,而是说给整个世界的。这时,他想冲出家门,跑到黎阳城南的山顶上,对着苍茫的天宇高喊几声:我要当兵!我要当兵! 小文填报过高考志愿的那天中午,父亲叫他过来,说让他看一样东西。 父亲拿出一个红绸小包,在小文面前慢慢打开。一个栩栩如生的泥陶小龙出现在小文面前。 父亲问:它叫什么? 伏龙肝。 为什么叫伏龙肝。 小文摇摇头。 咱老家的村子为啥叫郭宏屯? 小文又摇摇头。 小文便听到了一个壮怀激烈的故事: 隋末李密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中有一名叫郭宏的大将,他是咱家的先祖,先祖郭宏曾在咱老家的村子屯兵休整,这地方,自此就叫了郭宏屯。郭宏屯兵时,他的部属用泥塑一些人、马和小龙,以此怀念阵亡的战友。后来,这种泥塑艺术,就一代代传了下来。泥龙等塑像塑好后,要在炊中焙烤成陶,家乡将炊心土叫做伏龙肝,由于这泥陶是在炊中烧制的,不论塑的是龙,是人,还是鸟,就统称它为伏龙肝了。你看,伏龙肝的毛部有两个孔眼,吹一个会像海螺一样发出瓮声瓮气的鸣响。当初,起义军还将伏龙肝做号角用。据说,伏龙肝还有一大妙用,出门在外,如果不服水土了,刮些伏龙肝的泥陶末子,服了便好。我入伍那年,你爷爷给了我这个伏龙肝。上战场前,部队首长要求几次轻装,最后除了武器什么都轻装掉了,我却没丢掉这个伏龙肝。我知道,你爷爷让我带上伏龙肝,决不是担心我水土不服,伏龙肝,是咱郭家报效国家的精神图腾啊…… 父亲说下去了,他颤着手,将伏龙肝递给小文。 小文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,父亲会在几天后永远离开了他,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父亲死得很壮烈。很辉煌,那天,一个被通缉的杀人犯被发现后,劫持一辆出租车向城外逃跑,父亲驾着自己的车飞速追去,父亲的车超过那辆车时,一打方向将车横在路上,他想迫使罪犯停车。可丧心病狂的罪犯驾着车与父亲的车相撞起火。医院的路上,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,父亲的战友都赶来为他们的战友送行。那个白胖的叔叔代表父亲的战友泣不成声地讲了话。 送葬父亲那天,离小城五里地的郭宏屯的乡亲赶来三四百人。 当父亲的棺木被抬起时,郭宏屯村的父老乡亲吹响了一个个伏龙肝。 几百个伏龙肝的呜呜声像涛鸣、像海啸。 小文也吹响了父亲给他的那个伏龙肝。 (图片来自网络) 作者简介:马金章,河南浚县人,曾两次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。已在《十月》《北京文学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飞天》《广西文学》《雨花》《福建文学》《莽原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报刊发表出版文学作品多万字。多篇作品被《小说月报》《作家文摘》等选刊转载,《血型符号》、《臼声》、《伏龙肝》、《秀穗》曾被选入多省市高中语文试卷。已出版小说集3部,文化类图书28部。 第三故乡 编辑:仁武君 校对: 策划:淡墨浅痕(美篇号:) 收稿 投稿邮箱: qq.白颠风早期证状的图片治疗白癜风秘方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fulonggana.com/flgjbzl/93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210味常用中药名释义,表格版
- 下一篇文章: 脾胃为啥大城市的人易脾虚